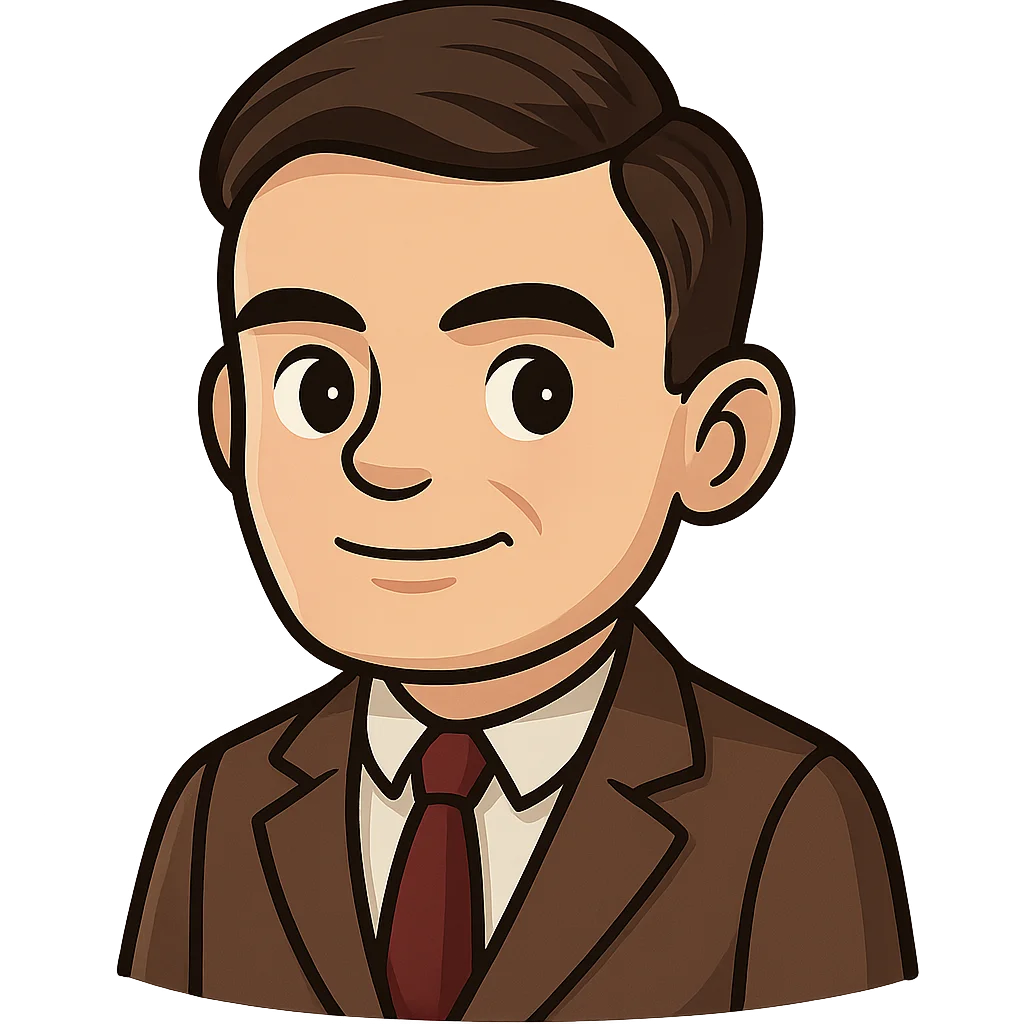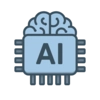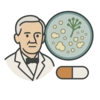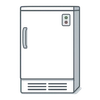艾伦·图灵:解码者
你好,我叫艾伦·图灵。我于1912年6月23日出生在伦敦,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巨大变革的边缘。从很小的时候起,我不仅对世界感到好奇,还决心要理解它的运作方式。当其他孩子还在玩简单的玩具时,我却对数字、模式以及支配一切的隐藏规则着迷。我非常热爱科学,为了能阅读关于科学的书籍,我很早就自学了识字。我用笔记本记录下自己的实验和想法,试图理解从植物如何生长到我们周围发生的化学反应等一切事物。
我的学生时代有时很艰难。我的脑子里总是飞速运转着各种复杂的问题,这常常让我在同学甚至老师眼中显得与众不同。他们希望我专注于传统科目,但我却被数学和科学深深吸引。我并不总是能融入集体,但我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朋友,他叫克里斯托弗·莫尔库姆。他和我一样对科学和伟大的思想充满热情。我们会花上好几个小时讨论从天文学到量子物理学的一切,梦想着我们有朝一日能做出的发现。他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我的思维方式。
不幸的是,在1930年,克里斯托弗病倒并去世了。失去他让我悲痛欲绝,但对他的怀念激发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我开始思考,是什么构成了人的心智——什么是意识?它是否可以被化学和物理学所捕捉?这个深刻的问题让我走上了定义我一生的道路:去理解思想的本质,并探索机器是否能够复制它。对克里斯托弗的怀念,坚定了我探索人类心智和逻辑本身最深层奥秘的决心。
我的学生时代结束后,我进入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在这里,我的思想终于可以自由地驰骋。在一些最伟大的数学家身边,我可以自由地探索逻辑和计算的抽象世界。正是在这段时间,也就是1936年,我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了一个后来成为我最著名的理论贡献的概念。我构想了一台“通用机器”,这是一台单一、简单的机器,只要给予正确的指令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程序,它就能解决任何问题、执行任何任务。这个想法,后来被称为图灵机,是今天所有计算机的理论蓝图。当时它纯粹是一台想象中的机器,但它为数字时代奠定了基础。
我的理论工作很快被一场非常现实的危机打断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我的国家需要我的帮助。我被招募到一个名为布莱切利园的绝密地点工作。那是一个乡村庄园,聚集了一支由数学家、语言学家和解谜专家组成的多元化团队,他们都为了一个关键任务而来:破解德国军方使用的密码。其中最难对付的是恩尼格玛密码。德国人使用一种特殊的恩尼格玛机来加密他们的信息,他们认为这种密码是无法破解的。机器的设置每天都在变化,产生了数十亿种可能的组合。我们每多一天无法破解密码,关于敌人计划的重要情报就会丢失,这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压力是巨大的。我们知道,那些杂乱无章的信息中隐藏着能够改变战争进程的秘密。我与一个杰出的团队合作,开发出一种破解恩尼格玛密码的方法。我的想法不是用笔和纸来解决,而是要制造一台机器来对抗另一台机器。我们设计了一种名为“炸弹机”的机电设备。这台机器体积庞大,充满了嗡嗡作响的转鼓和电线,它的任务是快速测试成千上万种可能的恩尼格玛设置。它将我们想出的逻辑过程自动化,以比任何人都快得多的速度寻找当天的正确密钥。这是一个巨大的谜题,而战争的命运就悬在我们每天能否解开它之上。
我们在布莱切利园的工作取得了成功。到1940年,“炸弹机”投入运行,我们能够破译大量的恩尼格玛信息。这些情报为盟军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优势,帮助他们在重大战役中获胜,并最终缩短了战争的进程,战争于1945年结束。战后的许多年里,我们在布莱切利园所做的一切仍然是严格保守的秘密。我们不能谈论我们的贡献,但我们知道我们改变了历史。
战后,我致力于将我的理论“通用机器”变为现实。我参与设计了世界上第一批电子计算机,比如自动计算引擎(ACE)。我梦想着未来这些机器不仅仅能计算数字;我想知道它们是否真的能够思考。这引导我探索我们现在称之为“人工智能”的领域。我甚至提出了一个测试,后来被称为图灵测试,用以判断一台机器是否能表现出与人类无异的智能行为。“机器能思考吗?”这个问题驱动着我的工作。
然而,我的一生并非没有巨大的挑战。在1950年代,世界对于与众不同的人并不总是那么包容,我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我的职业生涯被迫中断,我的生命也在1954年走到了尽头。我度过了充实的一生,但它结束得太早了。
虽然我没能亲眼看到,但我所梦想的那些思想已经塑造了现代世界。我通用机器背后的原理如今存在于每一部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计算机中。我的密码破译工作现在被誉为历史的关键部分。我的故事表明,有时候你能做的最强大的事情就是提出一个大胆的问题,并追随它到任何地方,即使你无法在有生之年找到所有答案。一个思想的种子,可以成长为改变后代一切的东西。
活动
参加测验
通过有趣的测验测试你所学的知识!
发挥你的创意,尽情上色!
打印此主题的涂色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