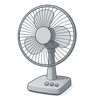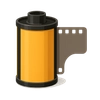会说话的电线
你们好. 我的名字是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我一生都对声音着迷. 我的母亲和心爱的妻子梅布尔都是失聪的. 她们的无声世界让我对听觉的本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毕生都在研究语音的振动,希望能以某种方式让声音对她们来说变得可见或可触摸. 在我生活的1870年代,世界是一个更加安静、节奏更慢的地方. 如果你想给远方的朋友传递信息,你得写一封信,而这封信可能需要数周才能送达. 或者,你可以发送一封电报,虽然速度更快,但只能传递由点和划组成的冰冷、没有人情味的编码. 我梦想着一种更高级的通讯方式. 我梦想着一台能够通过一根简单的电线,传递人类声音的温暖和情感的机器. 人们称之为“会说话的电报”. 这听起来就像魔法,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我坚信,如果我能理解我们的耳朵是如何将振动转化为声音的,那么我一定能制造出一只“机械耳朵”来完成同样的事情. 这个梦想占据了我的全部心神,它是我决心要解开的一个谜题.
我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实验室,既是我的避难所,也是我的战场. 那里一片混乱,到处都是电线、磁铁、电池和各种奇形怪状的装置. 在这场探索中,我并不孤单. 我有一位才华横溢、尽职尽责的助手,他叫托马斯·沃森,是个年轻人. 汤姆是一位天赋异禀的机械师,他的双手能将我脑海中的构想变为现实. 我们的日日夜夜,常常在希望与挫败的循环中度过. 我们会花上好几个小时来制造一个新的发射器,小心翼翼地缠绕线圈、调整薄膜. 然后我们会进行测试. 我会带着发射器进入一个房间,而汤姆则带着接收器进入另一个房间,一根长长的电线连接着我们俩的设备. 我对着我这一端说话,他则把耳朵紧紧贴在他那一端,专心致志地听着. 大多数时候,他听到的只是静电的嘶嘶声、噼啪声或是微弱而混乱的嗡嗡声. 失败是我们永恒的伴侣. 有无数个瞬间,我们都想过放弃.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如何将复杂的语音振动转换成变化的电流,然后再在另一端将这股电流转换回完全相同的振动. 这是一个从未有人解决过的难题. 但汤姆和我怀有同样执着的信念. 每一次失败的实验都教会了我们一些新东西,让我们离成功又近了微不足道的一小步. 我们是一场宏伟冒险中的伙伴,追逐着一个从未有人通过电线听过的声音.
突破是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到来的,那一天开始时和往常没什么两样:1876年3月10日. 当时我们正在研究最新的设计,一种液体发射器,它利用一根在酸化的水中振动的针来改变电流强度. 我在装有发射器的房间里,汤姆则在隔壁房间里,守在接收器旁等待. 就在我调整设备时,我的手滑了一下,不小心打翻了一罐电池酸液. 酸液溅了我一身衣服. 我吓了一跳,疼痛之下,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实验. 我本能地对着离我最近的发射器大喊:“沃森先生,快过来—我要见你.”. 我的话语只是一个简单而紧急的求助. 片刻之后,我听到了冲向我门口的脚步声. 是汤姆. 但他脸上并没有对我泼洒事故的担忧,而是充满了纯粹的、毫不掩饰的惊愕. “我听到你了.” 他说,声音因激动而颤抖. “我听到了你的话. 清清楚楚.”. 我花了一点时间才明白他这句话的含义. 他不是通过墙壁听到了我的喊声. 他是通过那台机器听到的. 溅出的酸液意外地形成了完美的电路连接,使得发射器能够极其清晰地捕捉到我声音的振动. 我们成功了. 经过多年的奋斗,我那会说话的电线的梦想,已不再是梦想. 它变成了现实.
那次意外的通话改变了一切. 就在那一瞬间,世界变小了. 人类的声音第一次通过电线传播,传递了清晰的信息. 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我们轮流对着机器说话和倾听,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喜悦和惊奇. 当然,我们的征程还没有结束. 我们必须向这个充满怀疑的世界证明,我们的发明不是什么戏法. 同年晚些时候,在费城的百年博览会上,我们向皇帝和科学家们展示了电话,他们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会说话的电报”不再是幻想. 从波士顿那个小小的实验室开始,一张电线网络最终将遍布全球,连接起家庭、企业和国家. 我的愿望始终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回首往事,我对沃森先生发出的第一条信息,不仅仅是一次求助. 它更是对未来的呼唤,是献给世界的声音,它证明了只要有足够的好奇心和毅力,即使是最不可能的梦想,也能够发出声响.
活动
参加测验
通过有趣的测验测试你所学的知识!
发挥你的创意,尽情上色!
打印此主题的涂色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