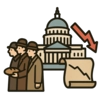大沼泽地:草之河的故事
想象一条河,宽到你看不见对岸,水流缓慢到你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是在陡峭的河岸之间流淌,而是在一片广阔平坦的土地上漫延。这条河不仅由水构成,还由草构成。高大、边缘锋利的锯齿草绵延数英里,轻抚着无垠的天空。这里那里,一丛丛的柏树从水中的小土丘上长出,看起来就像金色海洋中的绿色岛屿。在黎明和黄昏时分,我的空气中充满了交响乐般的声音——短吻鳄低沉的吼声、百万只昆虫的鸣叫声、涉水鸟类的戏水声,以及青蛙们合唱的夜曲。几千年来,我曾是古代民族的家园。卡卢萨人和特科斯塔人与我的节奏和谐共存。他们用贝壳堆成土丘,在上面建造家园,乘坐独木舟穿行于我的水路,并深谙我季节变化的微妙平衡。这些贝壳丘至今仍在这里,静静地提醒着人们,曾经有人作为我的一部分生活,而不是与我分离。大多数人看到我时,会觉得我是一片沼泽,但我其实是远比那更复杂和独特的存在。我是一条草之河。我是大沼泽地国家公园。
几个世纪以来,我的水流从奥基乔比湖自由地向南流入佛罗里达湾,滋养着沿途的一切。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种新的人来到了佛罗里达。他们看着我广阔湿润的土地,看到的不是一条赋予生命的河流,而是障碍。他们梦想着建造城市、道路和用于种植甘蔗和蔬菜的大片农场。对他们来说,我的水是需要被控制和排走的东西。于是他们开始挖掘。他们开凿了又长又直的运河,将我的水引向海洋,并修建了堤坝——高高的土墙——来阻挡我的季节性洪水。他们的目标是为自己创造出干燥、可预测的土地。但在改变我水流的同时,他们也开始改变我的心脏。那层定义了我几千年的缓慢、浅浅的水面开始在一些地方消失。在我健康的时候很少发生的火灾,在旱季时,干枯的锯齿草成了熊熊大火的燃料。那些依赖我的水塘里鱼虾螺蛳为生的大群涉水鸟类,如鹭和白鹭,发现它们的食物来源正在消失。我维持了数千年的微妙平衡正在被打破,我的未来变得不确定。
就在我狂野的灵魂似乎要被驯服并永远消失的时候,那些看到我真正价值的人们开始为我发声。我最伟大的捍卫者之一是一位名叫欧内斯特·F·科的男士。他是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景观设计师,于1925年搬到迈阿密。当他第一次探索我的荒野时,他被我独特的美丽迷住了。他看到的珍稀鸟类、强壮的短吻鳄和无尽的锯齿草,不是需要被征服的东西,而是需要保护的国家宝藏。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科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了我的事业。他给政治家写了无数封信,向社区团体发表演讲,并带领旅行团深入我的湿地,向人们展示危在旦夕的是什么。他不知疲倦地为提议中的国家公园规划边界,为他赢得了“大沼泽地国家公园之父”的称号。接着,另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加入了这场斗争。她的名字叫马乔里·斯通曼·道格拉斯,是一位在佛罗里达生活了几十年的记者和作家。1947年,她出版了一本开创性的书,《大沼泽地:草之河》。她用优美而科学的文字,告诉全世界我不是一片毫无价值的沼泽,而是一条复杂、赋予生命的河流。她的书永远地改变了人们对我的看法。这些捍卫者以及许多其他人的共同努力,慢慢扭转了局势。1934年5月3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建立该公园。又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1947年12月6日,哈里·S·杜鲁门总统来到佛罗里达,正式宣布我成为大沼泽地国家公园,确保我能为子孙后代得到保护。
今天,我是一个庇护所。我是一些美国最令人难以置信的生物的受保护家园。美洲短吻鳄在我的水域中悄无声息地滑行,温柔的海牛在我的运河里啃食水生植物,在我最偏远的角落深处,难以捉摸的濒危佛罗里达豹仍在漫游。我的重要性远超美国国界。1979年,我被命名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使我与大峡谷和大堡礁等地一同被列为地球上最珍贵的自然宝藏之一。但我的故事并未结束,我的挣扎也并未完全成为过去。很久以前修建的运河和堤坝仍然扰乱着我的自然水流。因此,今天,历史上最大的环境恢复项目之一正在进行,试图治愈我。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正在努力恢复那条作为我生命之源的、缓慢流淌的浅浅草之河。我是一个活的实验室,教导科学家如何修复一个受损的生态系统。不仅如此,我是一个野性的宝藏,每年提醒着超过一百万的游客关于自然世界的力量与美丽。我是一个关于坚韧的故事,是对那些为我奋斗的人们的证明,也是一个关于野生之地重要性的承诺。
活动
参加测验
通过有趣的测验测试你所学的知识!
发挥你的创意,尽情上色!
打印此主题的涂色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