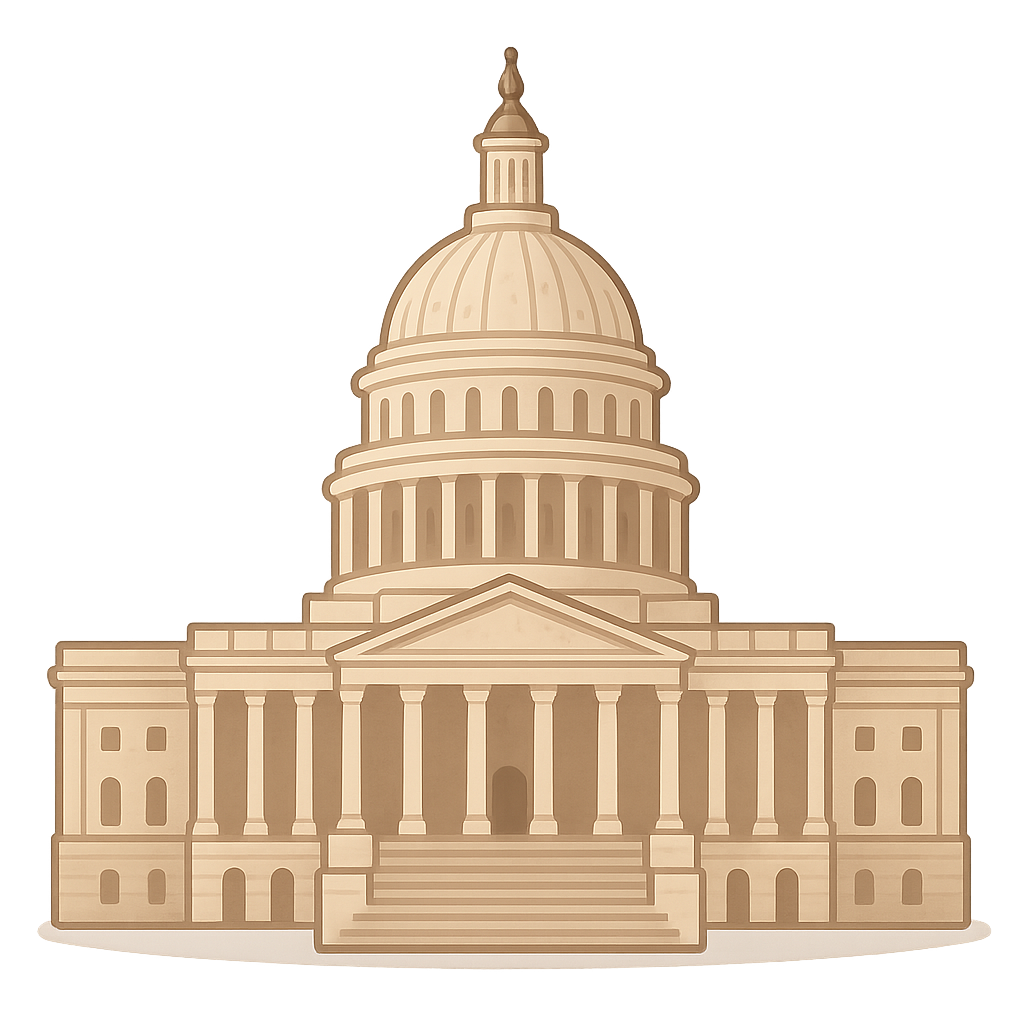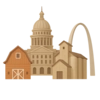一条河流的故事
我的旅程始于一个低语,一股来自北方一个叫做艾塔斯卡湖的清澈凉爽的细流。起初,我很小,小到孩子都能一跃而过。但当我向南流淌时,我从无数的溪流和支流中汲取力量,每一英里都变得更宽阔、更强大。我穿过森林,滚过草原,切割古老的岩石,像一条蜿蜒流淌的水带,横贯一个伟大大陆的心脏。几千年来,我见证了沿岸文明的兴衰。我承载过探险家的追求,推动过工业的车轮,也启发了诗人和音乐家。我的水域里藏着无数的秘密和故事,是一部关于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流动的历史。他们给我取过很多名字,但你们所熟知的那个名字是密西西比河。
早在第一艘欧洲帆船出现在地平线上之前,我的岸边就住着熟悉我每一个转弯和水流的人们。数千年来,原住民们围绕着我的节奏建立他们的生活。我记得密西西比文化,一个近千年前在这里繁荣的伟大文明。在密苏里河与我交汇的地方附近,他们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城市,你们现在称之为卡霍基亚。那是一个拥有数千人口的繁华都市,巨大的土丘像人造山脉一样耸向天空,其中最大的一座比当时这片土地上的任何建筑都高。对他们来说,我不仅仅是水。我是生命线,是神圣的精灵。我的水域为他们提供鱼类,为他们的玉米提供肥沃的土壤。我的水流是他们的高速公路,载着他们的独木舟在村庄之间进行贸易和举行仪式。他们用充满敬意的名字来称呼我,比如“Misi-ziibi”,意思是“伟大的河流”,或者“众水之父”。他们与我的联系是深刻的,一种尊重和依赖的纽带,塑造了他们世世代代的世界。
接着,变化来临了,由奇怪的新船帆上的风带来。1541年,一位名叫埃尔南多·德·索托的西班牙探险家和他的手下偶然发现了我的南部水域。他们正在寻找黄金和财富,把我视为需要跨越的障碍,而不是一位精神上的父亲。他们是第一批凝视我浩瀚的欧洲人,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多世纪后,在1673年,两位法国人带着不同的目的到来。传教士雅克·马凯特神父和皮草商人路易·若列划着独木舟顺着我的上游而下。他们寻找的不是黄金,而是知识——以及一条通往西部海洋的路线。他们仔细地绘制了我的路线图,记录了他们遇到的土地和人民。然后,在1682年4月9日,另一位坚定的法国人,勒内-罗贝尔·卡弗利耶·德·拉萨勒,完成了这段旅程。他和他的队伍走遍了我的全程,从寒冷的北方一直到我注入墨西哥湾的入海口。在那里,他插上了一面旗帜,为法国国王宣称拥有我整个广阔的流域。一个多世纪以来,我的未来与欧洲紧密相连,直到1803年,一个新兴的国家——美国,在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获得了这片土地。突然之间,我不再是殖民地的边疆,而是一个年轻、雄心勃勃的国家的中央动脉。
19世纪给我的水域带来了新的声音:蒸汽船的轰鸣声、翻滚声和汽笛声。这些喷着火的庞然大物,有着高耸的烟囱和巨大的明轮,彻底改变了我。第一艘从俄亥俄河一路航行到新奥尔良的,是1811年的“新奥尔良号”自己。突然之间,逆着我强大的水流航行成为可能,我成了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运送着棉花、糖和无数寻求新生活的人们。一个名叫塞缪尔·克莱门斯的年轻人爱上了这种生活,他学习我水下的每一个沙洲和暗礁,成为一名蒸汽船领航员。他后来取名马克·吐温,在他的书中写满了我的故事,与全世界分享我的精神。但我的重要性也带来了冲突。在美国内战期间,控制我至关重要。联邦和邦联为我的水域激烈战斗,1863年漫长而残酷的维克斯堡围城战是一个转折点。它的陷落让联邦控制了我的全长,将南方一分为二。在这场动荡中,另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我的三角洲诞生了。从在田间劳作的非裔美国人的悲伤与希望中,一种新的音乐——蓝调——诞生了。这种充满灵魂、痛苦和坚韧的声音,飘过我的水面,在新奥尔良市与活泼的节奏融合,创造了爵士乐。我的水流似乎在他们的音乐中流淌,这种声音将改变世界。
今天,我的旅程仍在继续,尽管我的同伴已经改变。优雅的蒸汽船大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强大的拖船,推着长长的驳船队,满载着谷物、煤炭和石油。曾经矗立着土丘的地方,如今耸立着拥有闪亮天际线的伟大城市。但我的力量依然未被驯服。我曾多次展示我的愤怒,最著名的是在1927年的密西西比大洪水中,那是一场毁灭性的事件,淹没了整个城镇,并促使人类建造了庞大的堤坝和溢洪道系统,试图控制我的水流。这些努力提醒着每一个人,我是一种需要敬畏的自然力量。我不仅仅是流向大海的水。我是与过去活生生的联系,是无数鱼类、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的家园,也是站在我岸边的梦想家们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我的水流中承载着一个大陆的故事,我向前流淌,怀抱着对未来的希望。我邀请你们倾听我的低语,并帮助照顾我,因为我的故事,也是你们的故事。
活动
参加测验
通过有趣的测验测试你所学的知识!
发挥你的创意,尽情上色!
打印此主题的涂色书页。